时光如梭,教育系从1981年开始招生,已经走过了41年的战斗历程。回想当年,教育学专业的老前辈们满怀信心和期望,迎接了恢复建系后的第一届学生。这在他们的言谈和举止当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尤其是金增先生代表全体教职员工在教育系首届迎新大会上的发言,给81级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因为如此,他们便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活动,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基本的滋养。
众所周知,对学校教育专业的学生而言,教育学是一门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按当时的教学计划,把它安排在跨学年两个学期的时间段里。其具体时间是从1981——1982学年的下学期,至1982——1983学年的上学期。起初是金增老师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主讲教学原理——教学论;随后是姜华老师讲授教育论。
金增老师的讲课风格十分独特,表达能力极强且有相当大的震撼力。不过,老先生的授课演讲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引领学生对热点问题的讨论,把被动的学习转变成一个主动的探索过程。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以及教学规律的探讨与争论,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向学生传递了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你要登台演讲,必须讲出点与众不同的东西,相近或雷同的问题不能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规矩。先生不在乎你没有自己的观点,相反他鼓励大家提出质疑。先生十分认可“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论断。有时是师生之间的争论,同时也有学生间的争论,互不相让面红耳赤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当年,听金增先生讲课的还有若干名新留校的青年教师和进修生,整个课堂挤得满满的,相反人们的想象根本没受狭小空间的限制,实现了自由的翱翔。
与今天的数字化、信息化水平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信息相对匮乏。然而,金老师在课堂上前沿信息的把握如数家珍,让我们充分了解了凯洛夫、苏霍姆林斯基、赞可夫、布鲁纳等大教育家们学术思想。除了课堂讨论,先生积极配合王继祯老师小学数学教改,带领学生深入一线听课、评课,接受实践的摔打与磨练。在此基础上先生还把王继祯老师请课堂上,介绍他小学数学教改的思路和方法,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课堂教学改革实践的认识。先生的教学重点在于教学论,课程结束时铅印了《教学论》初稿,也是老先生授课精华的结晶。除了课堂金老师对我们的后续影响也是很深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就是在呼市牵头组织召开了华东华北七院校教育学会议,让同学们领略国内学者们的学术风范。临毕业时,金老师的教育名著选读更有意义,进一步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
姜华老师的讲课风格,不急不躁、慢声低语、娓娓道来。他讲授的教育论,基本上是提纲挈领,贯彻了教是为了不教的思想,而且课堂讨论或学生登台演讲所占的比重更大。一些没有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过话的同学,还是有点不适应。不过金增老师打下的底子或提供的训练,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年我们是蒙汉生合成一般班,中小学阶段一直用蒙古语授课的同学,一下改为汉语表达却有一定的难度。不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化练兵,使他们从生到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单元,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一些说话不连贯且带有方言韵味的汉授生,也逐步趋向普通话,有了明显的改观。为了做好讨论的准备,前往图书馆借书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当年的图书借阅基本上都是用手工检索,即便这样他们也能够找到自己所需书籍。我在想难道他们把借来的书都读了吗?答案是不确定的。不过他们至少过了一个浏览、粗读的手续,事实上这就达到了目的。另外,课堂讨论在客观上提高了同学们的文字能力和水平,为日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等到结课的时候,姜老师拿出了一本由校内铅印的《教育论》初稿,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资料。姜老师课堂以外的功夫是,与所有同学们的交往还是比较到位的。若干年后,老先生还能记住同学们的名字。
金老师和姜老师的教学合二为一,在最后的评价上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两位先生放弃了传统的笔试,取而代之的是口试。为了做好口试,两位先生事先准备了大量的试题,以备每个人的抽取和应答,而且做到了前后不重复。试题的形式以简答或论述为主,重点看学生的反应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并以抽签的方式有序推进,回答问题不得超时。说句实话,这种考试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也是教育系教学史上的第一次。由于它是首创,很多人都没经历过,因此都很紧张。结果口试下来,每一位同学都是面带微笑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表现得都很理想。本次口试整整持续了一整天,两位老师在疲惫的同时也收获了一种喜悦。
靳乃铮先生是从1983——1984学年的下学期至1984——1985上学期,给81级同学们讲授了“中国教育史”。所用的教材是,北京师范大学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写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之前,先生与我们班很少有面对面的交流,原因是他在北京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的编写任务,在时间上很难错开。不过,人们对先生的学识和声望如雷贯耳,期待着先生能够早日出现在讲台上给大家传经送宝。先生的《重新学习党的教育方针》[1]、《教育的本质与归属》[2]、《谈正确对待我国古代教育遗产问题》[3]等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学们对此都有所感悟或拜读。
在当时的条件下,靳老师在课堂上因陋就简挂图用的比较多。其思路是重点考虑到部分蒙古语授课同学们的实际,把那些古文段落写在纸上,等到用的时候把它挂在黑板上逐字逐句地加以解释,让人看后透彻明了。好在之前我们上过一学期的古代汉语课,有了一些基础。这些与实际阅读文献,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给我的感觉先生讲中国教育史的长项在于:一是熟悉文献史料;二是实地考察过部分名胜古迹;三是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先生在讲课时吟诵的一些古诗词和自己创作的诗文,不仅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教育史课的内在魅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生书本以外的学术考察阅历,为我们客观地复原教育的个别历史场景,使得抽象的东西变成了直观,缩短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
应该说,靳老师的课对我个人的促动特别大。我的最大收获是通过这门课学习,找到了教育与历史相衔接的一个切入点。我发现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写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具有明显的不足。这本书在题目上列有“宋元明时期的教育”,但元代教育内容却寥寥无几。为此先生也给予了演讲和点拨,不过仍然留下了好多疑惑不解的东西。等到毕业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撰写论文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先生现身说法给我们上了一次“如何撰写学术论文”的专题课。记得那次先生真的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实货,自己代表作的手稿。其中有一稿、二稿、三稿、四稿等等,用毛笔字涂涂画画,有的就直接予以了删除。这些书稿告诉我,什么叫科学研究,怎么叫做学问,整个过程深深地印刻我的脑海里,成了一个永远的记忆。这样,我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为“元代的教育”,并得到了先生的指导,最终获得“上乘之作”的评价。从那个时日起,我便走上了研究北方游牧民族教育史的道路。
李屏西先生在1983——1984学年的上学期,给我们讲授了心理学史课。先生的学术功底很深,也是我国心理学界有影响力的专家。他一生中发表论文、译文20余篇;上世纪50年代,参考苏联心理学集体编写了专修班心理学教材;1980年,参加教育部主办的高等师范院校心理学专业统编教材《西方近代心理学史》的编写工作;1981年,与人合写的论文《中国古代脑髓说的萌芽与王清任脑髓说的突出成就》,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入选潘菽主编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一书[4]。先生的这些学术积累,为他讲授心理学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做到了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先生酷爱教育,尤其在课堂上从来都不顾及自己的哮喘,将这门课的思想体系、理论框架、人文情怀、前沿动态,梳理的极为详尽。通过先生的讲授,我们较全面地把握了西方心理学发展的脉络及其相关人物贡献。费希纳、冯特、铁钦纳、威廉•詹姆士、华生、弗洛伊德等诸多心理学人物及其学派的介绍,让我们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教材是,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先生的教学实践证明,这只是一本参考书。在具体施教过程中,先生从未受制于这部教材。他杜绝了不是面面俱到和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有所侧重地向学生传递了学术信息,而且有意识地融入了他个人的研究成果。1989年先生编写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专题选编》[5],应该是他多年从事教学的结晶。
先生在教学过程中,还有意识地引领同学们向科学研究方向努力。我受先生的影响,围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相关问题写了一篇短文,为此先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但因资料的缺乏成为一个习作而告一段落。若干年后,回想起这一事情,自己的努力还没到位。与此同时自己的兴趣爱好已经转向了中国教育史而淡化了这一领域。从客观上讲,先生的授课侧明显地重于西方心理学史,而对中国心理学史有所简化,然而其后续的教材恰恰是与之相反。“亡羊补牢犹未迟也”[6],这是对后学的一种激励。
王乃忱老师在1983——1984学年的上学期,给我们讲授了小学语文教学法;1984——1985学年的上下两个学期,讲授了外国教育史。王老师的小学语文教学法,恰好安排在小学实习之前,因此针对性很强。在某种程度上是战前动员,或曰实战演习。王老师对这门课程的定位是两个字——实践,其实这一思路是相当准确的。前人积累的知识经验,对学生来说都是一个间接经验,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还需要以学生的直接经验作为支撑,用实践来加深认识。“教学有法,且无定法”,这是教学理论上提出的一个科学论断。他人成功的教学经验或方法,只是一个参照,好多具体的东西还有待于摸索和探讨。因此,王老师的课是精讲巧练,而且把重点放在了后者,将学生推到了前台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之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的操练使同学们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教学技能。与之相适应,到小学听课、评课、讨论,也成为常规教学的一项内容。正因为有了训练,等到同学们深入小学实习时,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赢得了实习学校任课教师和学生的好评。
王老师对外国教育史的讲授,扮演的是一个导演、教练员、评判员的角色。她提前安排授课的内容,然后要求学生自己备课登台演讲。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背后蕴含了很深的哲理。同学们为了表现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必须在备课环节上下功夫。每当这个时候,首先必须搜集大量的资料,然后进行加工整理,写出相应的讲稿以备登台演练。王老师对学生的评议,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艺术性。总的来讲,积极放大优点和亮点,以褒奖、鼓励、期望为主,说多怕伤了学生的自尊。然而有问题的时候,不是当着大家的面讲,而是私下交流沟通。另外,王老师在课堂以外,对学生的关心也很突出。记得1984年元旦,81级每一位同学都收到了一份王老师的一份贺卡,表达了她对每一个人的祝福和希望。当我们毕业30年相聚的时候,王老师还念叨着因事未到场的个别同学的名字。
王继祯先生在1983——1984学年的下学期,给我们小学算术(这是原始资料里的记载,而不是数学)教学法。先生早年在数学系开设过解析几何、数学分析、实变函数、中小学数学教材教法;1957年开始利用高中等数学思想和方法,从事更新小学数学基础理论的研究;1970年编写出教材在区内外进行了系统的实验[7]。总而言之,先生积极从事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实验,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因此他的讲授课程,基本上以专题形式推进。在小学数学教材中,渗透的集合论的思想,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思维模式。先生以火柴棍为例,实施的数码的教学,将抽象阿拉伯数字的进位问题,比较直观地摆在小学生面前。记得先生的小学数学教改实验,在西安的大雁塔小学得到了大面积推广。仅此一点,先生名声大振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金增教授在呼和浩特新城区满族小学进行的小学数学教改实验,不同程度地吸纳了王先生思想的精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信息的闭塞,王先生过世后大雁塔方面,仍有很多信件频繁地发给先生工作过单位。遗憾的是,这些信件都堆在那里,比较客观地见明了先生所取得的教改成绩。
东拉西扯说得比较杂,其本意在于“不忘初心”,通过回顾先辈们为教育系的建设和发展,在三尺讲台上铸就的人生辉煌,提炼出一个精神文化以便激励后学。在教育系数十年的征程当中,已故的老前辈们无怨无悔甘当铺路石,更重要的是为同学们的向上登攀提供了坚实的阶梯。假如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后继的学子们在学术的道路上,很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的摸索。内蒙古师范大学隆重庆祝七十年大庆之际,怀念已故的老先生们别有一番意义,愿他们的在天之灵永远保佑徒子徒孙们向更高的理想境界冲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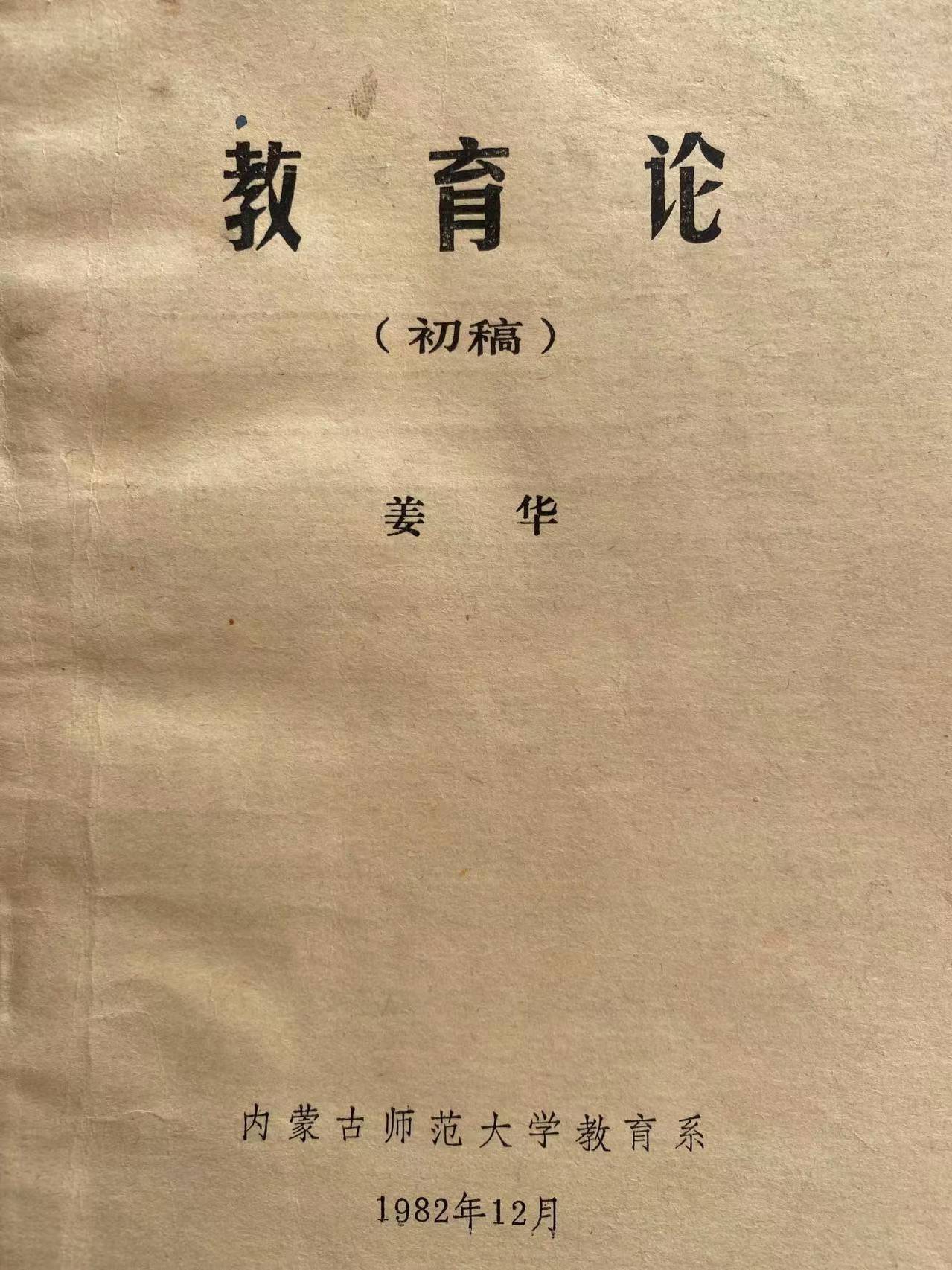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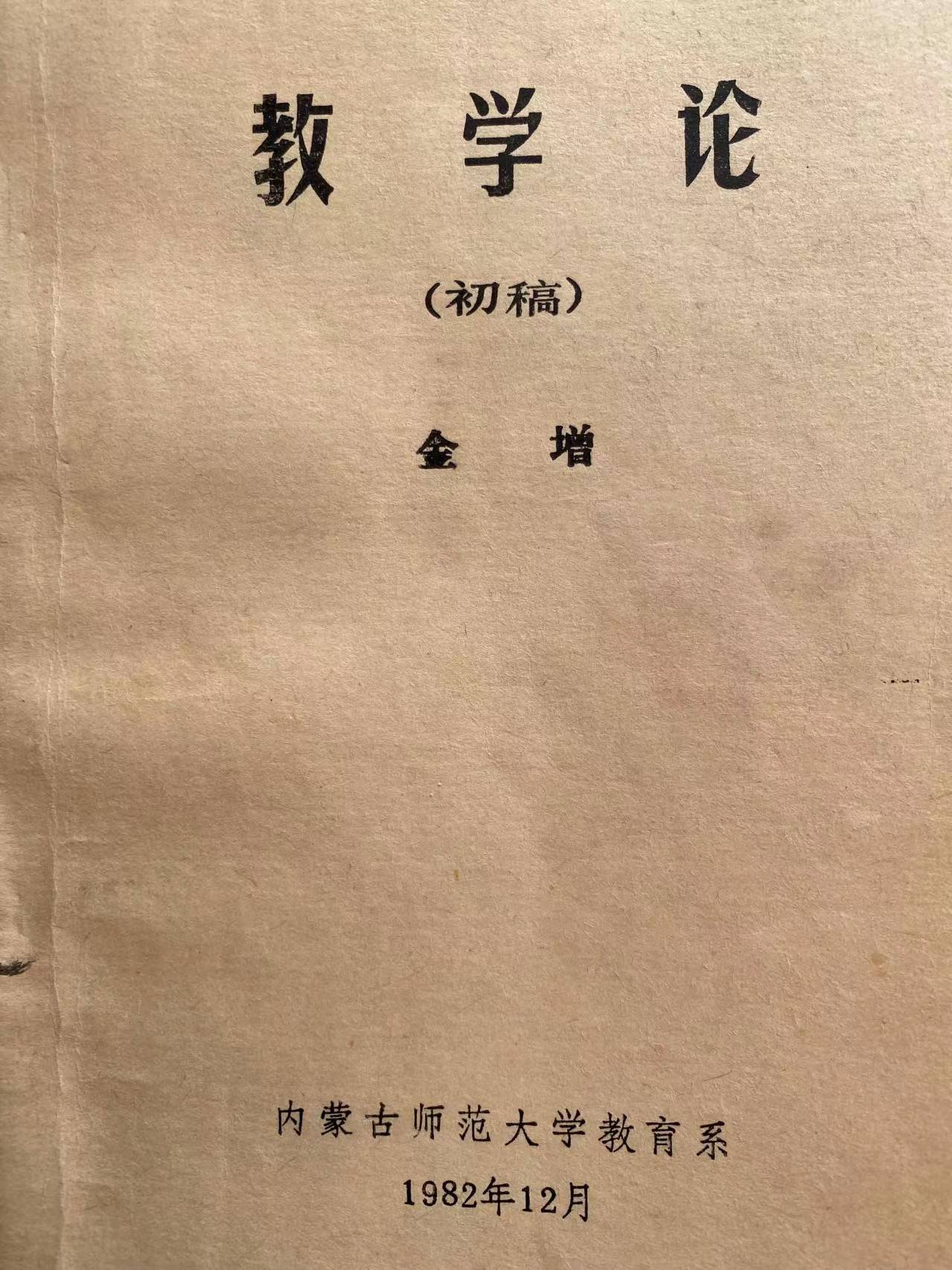
[1] 靳乃铮《重新学习党的教育方针》,载于《教育研究》,1981年第7期
[2] 靳乃铮《教育的本质与归属》,载于《教育研究》,1982年第6期
[3] 靳乃铮《谈正确对待我国古代教育遗产问题》,载于《教育研究》,1983年第3期
[4] 窦伯菊主修、刘成法主纂《内蒙古师范大学志1952——199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687页
[6] (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十七《楚四•庄辛谓楚襄王》(全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56页
[7] 窦伯菊主修、刘成法主纂《内蒙古师范大学志1952——199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2页
作者简介:
王风雷, 1985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系并留校任教;1998年晋升为副教授;2000年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2001年任硕士生导师;2003年任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主任;2004年晋升为教授;2010年任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族教育史研究所”所长;2013年任课程教学论学位点主任;2017年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及中国蒙古学学会理事、内蒙古家庭与社区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